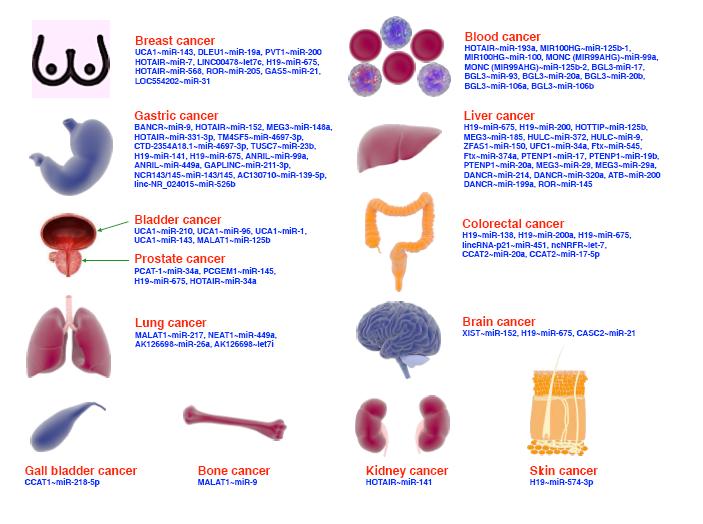| 1. |
Stheneur C, Laffond C, Rioux S, et al. Recent progress in Marfan syndrome. Arch Pediatr, 2012, 19(5): 551-555.
|
| 2. |
Bentall H, De Bono A. A technique for complete replacement of the ascending aorta. Thorax, 1968, 23(4): 338-339.
|
| 3. |
Coselli JS, LeMaire SA, Preventza O, et al. Outcomes of 3309 thoracoabdominal aortic aneurysm repairs. J Thorac Cardiovasc Surg, 2016, 151(5): 1323-1337.
|
| 4. |
宮漢東, 汪曾煒, 張仁福, 等. 升主動脈瘤臺并主動脈瓣關閉不全的外科治療. 中華心胸血管外科雜志, 2001, 17(3): 13.
|
| 5. |
Finkbohner R, Johnston D, Crawford ES, et al. Marfan syndrome. Long-term survival and complications after aortic aneurysm repair. Circulation, 1995, 91(3): 728-733.
|
| 6. |
Ince H, Rehders TC, Petzsch M, et al. Stent-grafts in patients with Marfan syndrome. J Endovasc Ther, 2005, 12(1): 82-88.
|
| 7. |
Nordon IM, Hinchliffe RJ, Holt PJ, et al. Endovascular management of chronic aortic dissection in patients with Marfan syndrome. J Vasc Surg, 2009, 50(5): 987-991.
|
| 8. |
Dong ZH, Fu WG, Wang YQ, et a1. Retrograde type A aortic dissection after endovascular stent graft placement for treatment of type B dissection. Circulation, 2009, 119(5): 735-741.
|
| 9. |
Waterman AL, Feezor RJ, Lee WA, et al. Endovascular treatment of acute and chronic aortic pathology in patients with Marfan syndrome. J Vasc Surg, 2012, 55(5): 1234-1240.
|
| 10. |
Eid-Lidt G, Gaspar J, Meléndez-Ramírez G, et al. Endovascular treatment of type B dissection in patients with Marfan syndrome: mid-term outcomes and aortic remodeling. Catheter Cardiovasc Interv, 2013, 82(7): E898-E905.
|
| 11. |
Cooper DG, Walsh SR, Sadat U, et al. Treating the thoracic aorta in Marfan syndrome: surgery or TEVAR? J Endovasc Ther, 2009, 16(1): 60-70.
|
| 12. |
趙紀春, 黃斌, 袁丁, 等. 外科聯合腔內雜交手術治療馬凡綜合征所致復雜胸腹主動脈夾層動脈瘤一例. 中華普通外科雜志, 2014, 29(6): 483-484.
|
| 13. |
唐驍, 符偉國, 郭大喬, 等. 馬凡氏綜合征心血管病變的外科分期治療 1 例報道. 臨床急診雜志, 2013, 14(3): 108-110.
|
| 14. |
Lipscomb KJ, Smith JC, Clarke B, et al. Outcome of pregnancy in women with Marfan's syndrome. Br J Obstet Gynaecol, 1997, 104(2): 201-206.
|
| 15. |
Eilen B, Kaiser IH, Becker RM, et al. Aortic valve replacement in the third trimester of pregnancy: case report and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Obstet Gynecol, 1981, 57(1): 119-121.
|
| 16. |
舒暢, 方坤, 黎明, 等. 晚期妊娠和產褥期主動脈夾層的腔內修復治療. 中國普通外科雜志, 2013, 22(12): 1541-1547.
|
| 17. |
楊璞玉, 張軍, 李燕娜, 等. 合并主動脈夾層的馬凡綜合征孕婦的妊娠結局分析. 中華婦產科雜志, 2015, 50(5): 334-340.
|
| 18. |
Grabenw?ger M, Alfonso F, Bachet J, et al. Thoracic endovascular aortic repair (TEVAR) for the treatment of aortic diseases: a position statement from the 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Cardio-Thoracic Surgery (EACTS) and the European Society of Cardiology (ESC), in collaboration with the European Association of Percutaneous Cardiovascular Interventions (EAPCI). Eur J Cardiothorac Surg, 2012, 42(1): 17-24.
|
| 19. |
Preventza O, Price MD, Amarasekara HS, et al. Chronic type Ⅰ and type Ⅲ aortic dissections: a propensity analysis of outcomes after open distal repair. Eur J Cardiothorac Surg, 2018, 54(3): 510-516.
|
| 20. |
Kalkat MS, Rahman I, Kotidis K, et al. Presentation and outcome of Marfan's syndrome patients with dissection and thoraco-abdominal aortic aneurysm. Eur J Cardiothorac Surg, 2007, 32(2): 250-254.
|
| 21. |
LeMaire SA, Carter SA, Volguina IV, et al. Spectrum of aortic operations in 300 patients with confirmed or suspected Marfan syndrome. Ann Thorac Surg, 2006, 81(6): 2063-2078.
|
| 22. |
張良, 于存濤, 常謙, 等. 常溫非體外循環胸腹主動脈置換術治療廣泛主動脈瘤. 中華外科雜志, 2016, 54(2): 119-124.
|
| 23. |
孫立忠, 程力劍, 朱俊明, 等. 常溫非體外循環下全胸腹主動脈替換術. 中華胸心血管外科雜志, 2011, 27(12): 705-708.
|
| 24. |
Juthier F, Rousse N, Banfi C, et al. Endovascular exclusion of patch aneurysms of intercostal arteries after thoracoabdominal aortic aneurysm repair. Ann Thorac Surg, 2013, 95(2): 720-722.
|